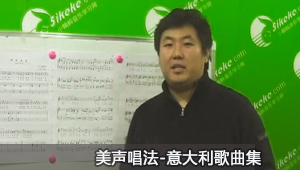陜北民歌與《東方紅》
這是一部用老镢鐫刻在西北黃土高原上的傳世巨著。它所達(dá)到的思想藝術(shù)境地,是人們所難以想象的。它以那難以名狀的奧妙留給人們一種特殊的美感享受。它是中華民族的一塊引為自豪的藝術(shù)瑰寶。
它,便是陜北民歌。
陜北民歌是陜北勞動(dòng)人民的精神、思想、感情的結(jié)晶,是陜北人民最親近的“情人”伴侶。陜北民歌歷經(jīng)滄桑而不衰,并不斷發(fā)展,源于它旺盛的生命力,生命力就來(lái)自它強(qiáng)烈的人民性。
陜北民歌的天才的作家們,大都是勞動(dòng)人民出身,就如同母親和她腹中的嬰兒一樣,勞動(dòng)人民將他們的思想感情源源不斷地輸入民歌之中,賦予了民歌充足的養(yǎng)分,使之健康地成長(zhǎng),他們與它結(jié)成了深厚的母子般的情誼。
在陜北,不論表現(xiàn)喜、怒、哀,樂(lè)哪種情感,都是有歌有曲的。夏天,在綠格英英的山上或重山峻嶺之巔,隨處都可以聽(tīng)到順風(fēng)飄來(lái)的悠揚(yáng)歌聲;冬天,在白格生生的雪原中,無(wú)論在曲曲彎彎的山道里或在一馬平川的大路上,趕牲靈的人們一路走一路歌,把人們從那寒冷、荒漠的天地中呼喚到今人心曠神怡的童話般的境界,在村莊里,有坐在墻畔編草帽、納鞋底的婆姨們的低婉吟唱,也有后生們的“攔羊嗓子回牛聲”的高歌回蕩。民歌,在這地瘠民貧,交通不便的偏僻山溝溝里,在幾千年的歷史長(zhǎng)河中,是陜北勞動(dòng)人民抒發(fā)感情的最好手段。“饑者歌其食,勞者歌其事”,它是發(fā)自人民心底的呼聲,可謂人民生活的第二種語(yǔ)言了。
“千年的老根黃土里埋”,“黃河畔上靈芝草”,陜北民歌就是深扎于勞動(dòng)人民心中的千年老根,就是勞動(dòng)人民心中的一棵靈芝草。有什么心里話,他們總是說(shuō)給它聽(tīng);有什么愿望,總是講給它聽(tīng)。陜北民歌成了記錄陜北勞動(dòng)人民真實(shí)思想、感情、愿望和理想的總譜,是陜北勞動(dòng)人民生活的最直接反映。
民歌,出自勞動(dòng)人民的心靈,在長(zhǎng)期的流傳發(fā)展中,又經(jīng)萬(wàn)人之口,通萬(wàn)人之心,每個(gè)人都將自己的精神甘露呈獻(xiàn)給了它,因而,它成了勞動(dòng)人民的思想、感情、愿望和理想的海洋。
階級(jí)壓迫和階級(jí)反抗,是封建社會(huì)、半封建社會(huì)生活的重要內(nèi)容。陜北民歌從各個(gè)方面反映了勞動(dòng)人民悲慘的生活,表達(dá)了勞動(dòng)人民對(duì)統(tǒng)治階級(jí)的憤怒和反抗情緒。著名的《攬工調(diào)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。它將階級(jí)的壓迫和剝削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來(lái),發(fā)出了“攬工人兒難!哎喲攬工人兒難!”的憤怒呼喊,感情的洪流如火山爆發(fā)、噴涌而出。反映勞動(dòng)人民悲慘生活和命運(yùn)的作品俯拾皆是,不勝枚舉,如《賣娃娃》,《民國(guó)十七年》、《腳夫調(diào)》等,這些民歌唱來(lái)凄慘、悲涼,人們眼前仿佛看到了一個(gè)個(gè)流淚苦訴身世的陜北農(nóng)民的形象,聽(tīng)到歌中一聲聲的悲嘆。真是一字一掬淚啊!在那萬(wàn)惡的舊社會(huì),勞動(dòng)人民誰(shuí)都有一腔難訴的苦!
在長(zhǎng)工歌里,流露出一種哀傷的情調(diào),長(zhǎng)工歌起于這個(gè)基調(diào),顯示了勞動(dòng)人民對(duì)這種生活的憤恨與無(wú)奈。“掌柜的你在那家里盛,堪乎兒累死我長(zhǎng)工”,“掌柜的穿的夾襖套背心,堪乎兒凍死我長(zhǎng)工”等,這是長(zhǎng)工們痛苦的呻吟。
訴苦歌,在陜北民歌中占有一定數(shù)量,這是一個(gè)淚的海洋,《走西口》便是其中的代表作。它敘述了一位名叫蔡長(zhǎng)生的青年醫(yī)生治好一個(gè)名叫孫玉蓮的姑娘的病,兩人產(chǎn)生了愛(ài)情,結(jié)為夫妻,婚后不久,因遇荒災(zāi),衣食無(wú)著,蔡長(zhǎng)生走西口謀生,夫妻灑淚相別的故事,《賣娃娃》寫了陜北一次大荒災(zāi)中,一個(gè)逃荒的男人賣掉自己的兩個(gè)孩子的故事,賣掉孩子,是為孩子謀條生路。歌中描寫的情景,十分凄慘:“可憐實(shí)可憐,可憐我沒(méi)有錢。量得二斗糠炒面,一風(fēng)吹上了夭。”賣孩子時(shí),父親“手拖五歲女,懷抱三歲男,丟下這個(gè)抱那個(gè),叫我好不難!”真是慘不忍睹。這些歌,是封建社會(huì)勞動(dòng)人民生活悲劇的再現(xiàn)。
勞動(dòng)人民不會(huì)做任人宰割的牛羊,他們的反抗情緒也會(huì)迸發(fā),反映在他們的行動(dòng)和語(yǔ)言上。
李自成領(lǐng)導(dǎo)的農(nóng)民起義源發(fā)于陜北。數(shù)百年來(lái),李自成一直被統(tǒng)治階級(jí)視為是犯上作亂的人,稱之為“李匪”。然而,在陜北勞動(dòng)人民的歌子中,“李匪”卻一直被作為英雄歌頌著,如酒曲《遠(yuǎn)阻米脂城》。
陜北人民為陜北出了這個(gè)英雄而驕傲,將他比做神龍出世,面將那些封建統(tǒng)治階級(jí)比作者鼠、狐貍。他們欺壓百姓,像老鼠狐兒子一樣到處打洞,沒(méi)想到竟然放出了壓在地下的神龍李自成,造了他們的反!陜北人民寄向在于英雄,寄反抗情緒于英雄,使這首民歌傳數(shù)百年而不衰,至今仍散發(fā)著熠熠光彩。
20世紀(jì)20年代始,中國(guó)大地上卷起了一場(chǎng)特大的“風(fēng)暴”,那就是中國(guó)共產(chǎn)黨領(lǐng)導(dǎo)的土地革命。這場(chǎng)風(fēng)暴也毫無(wú)例外地席卷了陜北高原,它把那里的社會(huì)徹底翻了個(gè)過(guò)兒,把“世事顛倒顛”了。社會(huì)的激烈動(dòng)蕩、變革,為陜北民歌譜寫新的一頁(yè)。
“陜甘游擊隊(duì),老謝總指揮”,這是1934年前后在陜北廣為流傳的民歌佳句。其實(shí),早在此10多年前,陜北的土地革命就已開(kāi)始了。陜北歷經(jīng)了土地革命、抗日戰(zhàn)爭(zhēng)、解放戰(zhàn)爭(zhēng)三個(gè)歷史階段。陜北是中國(guó)革命的根據(jù)地、大后方,它在中國(guó)革命斗爭(zhēng)史上占有光輝、特殊的位置。
這一時(shí)期的民歌,幾乎都是以中國(guó)共產(chǎn)黨所領(lǐng)導(dǎo)的中國(guó)革命斗爭(zhēng)為題材的。“他是人來(lái)咱是人,為甚他官咱們窮?為甚把咱的血汗直抽盡?”──講的是階級(jí)剝削的道理;“官逼民眾造反,世事大動(dòng)亂,他把咱老百姓沒(méi)殺完”──號(hào)召民眾起來(lái)革命;“軍隊(duì)百姓?qǐng)F(tuán)結(jié)牢,抗日救國(guó)呀心一條”──軍民團(tuán)結(jié),抗日救國(guó);“黃河浪起風(fēng)云涌,大海蛟龍要騰空。中國(guó)人民要掌政權(quán),解放軍大反攻”──講的是國(guó)家斗爭(zhēng)形勢(shì)……這一時(shí)期的民歌抒發(fā)了勞動(dòng)人民的反抗情緒,陜北人民再也不是悲劇性人物了,他們拿起了槍,向統(tǒng)治階級(jí)猛烈開(kāi)火了,那氣概,大有“蟠龍臥虎”之勢(shì);“千里的雷聲萬(wàn)里的閃,咱們革命的力量大發(fā)展”,“前不讓他前來(lái),后不讓他出”,“關(guān)住個(gè)大門好打狗”,“盒子槍,迫擊炮,打得那敵人沒(méi)處藏,叫聲敵人你快繳槍”等,其斗志之昂揚(yáng),氣吞山河,充分體現(xiàn)了陜北民歌所具有的時(shí)代性。
這一時(shí)期的民歌,均源于作者的親身經(jīng)歷,是作者強(qiáng)烈感受到的東西,抒發(fā)的是作者的真情實(shí)感,因此,歌子真實(shí)、強(qiáng)烈、自然、悠遠(yuǎn)綿長(zhǎng)、質(zhì)樸明快。如1943年,在延安召開(kāi)了陜甘寧邊區(qū)勞模大會(huì),勞動(dòng)英雄孫萬(wàn)福見(jiàn)到毛主席后,激動(dòng)萬(wàn)分,拉著毛主席的手說(shuō):“大翻身哪!有了吃,有了穿,帳也還了,地也贖了,牛羊也有了……沒(méi)有您,我們這些窮漢趴在地上一輩子也站不起來(lái)!”他有感面發(fā),創(chuàng)作出著名的民歌《咱們的領(lǐng)袖毛澤東》:
高樓萬(wàn)丈平地起,
蟠龍臥虎高山頂,
邊區(qū)的太陽(yáng)紅又紅,
咱們的領(lǐng)袖毛澤東。
再如,舉世聞名的《東方紅》原名叫《移民歌》。它最早的內(nèi)容是一首情歌,后由民間歌手李有源改編創(chuàng)作而來(lái)。
黃河,5000年古國(guó)文化的發(fā)源地。詩(shī)人們稱它為“中華民族的搖籃”。
《東方紅》的作者李有源,就出生在這偉大的河流──黃河畔上陜西葭縣的一個(gè)貧民家庭。
李有源的父親常年給地主當(dāng)長(zhǎng)工,家境非常貧寒。為了一家老小有個(gè)安身的地方,全家人一塊塊地打石頭、背石頭,才箍好了一孔窯洞,李有源的父親終因生活逼迫,勞累成疾而死去。李有源的母親帶著三個(gè)孩子掙扎在死亡線上。
一個(gè)人的幼年生活,該有多少樂(lè)趣啊,而李有源首先嘗到的,卻只是人間的辛酸。
從16歲起,李有源擔(dān)負(fù)起全家的田間勞動(dòng)。對(duì)莊稼來(lái)說(shuō),水和肥料是不可缺少的東西。然而,在那個(gè)時(shí)候,眼看著田間的禾苗日益干枯,眼望著黃河的水,依然是滔滔東流,但它對(duì)莊稼卻一無(wú)所用,只能白白地流去。人們嘆息著,只有祈禱老天爺能帶來(lái)好收成。李有源從早忙到晚,從春忙到冬,然而一家人卻始終吃不上一頓飽飯。李有源常常對(duì)著滔滔的河水發(fā)出呼喊:“老天爺,你為什么不睜開(kāi)眼?”
生活的重?fù)?dān),井沒(méi)有阻擋李有源念書(shū)識(shí)字的愿望,炕上、地下、河邊、山坡都是李有源學(xué)習(xí)的課堂,說(shuō)本、唱同都成為了李有源學(xué)習(xí)的課本。
陜北是民歌豐富的地方,生長(zhǎng)在民歌之鄉(xiāng)的李有源,從小就聽(tīng)?wèi)T了民歌的抒情、活潑的節(jié)奏,也聽(tīng)?wèi)T了人們向往美好生活的歌聲。李有源在生產(chǎn)和生活中,積累了豐富的閱歷和經(jīng)驗(yàn),因此,他自然地學(xué)會(huì)了用民歌形式,去反映人們的思想。情感和愿望。
劉志丹領(lǐng)導(dǎo)的游擊隊(duì)伍上了演山,漫山遍野響起了激動(dòng)人心的歌聲。土地革命鬧開(kāi)了,毛主席到達(dá)陜北了……
這些振奮人心的消息,閃電般地傳開(kāi)了。照例,幾個(gè)知己、說(shuō)得來(lái)的莊稼人,在深夜的窯洞里,熱烈地談?wù)撈饋?lái)。這一夜他們談?wù)摰牟皇恰叭龂?guó)”,也不是李自成進(jìn)北京,而是一個(gè)嶄新的話題:
“紅軍快到咱們這兒了!”
“……毛主席來(lái)到了陜北,咱們窮人這下有指望了。”……
李有源回到了自己的破窯洞。這一夜,他的心里很不平靜。
“百聞不如一見(jiàn)”,就在去葭縣城的路上,李有源親眼看到了紅軍,前面紅旗飄揚(yáng),后面人馬浩浩蕩蕩。所有的紅軍都赤著腳,穿著草鞋,分不清哪個(gè)是官,那個(gè)是兵,看起來(lái)和莊稼人一模一樣。他們扛著槍,個(gè)個(gè)精神抖擻,雄赳赳,氣昂昂,從霞縣城下,東渡黃河。
從來(lái)沒(méi)有見(jiàn)過(guò)這樣的隊(duì)伍。你看,他們見(jiàn)了莊稼人多么親熱!李有源不知什么時(shí)候放下了糞桶,和人們一起歡呼起來(lái)……
啊!他們就是奔赴抗日前線的人民軍隊(duì)!他們就是毛主席共產(chǎn)黨領(lǐng)導(dǎo)的救國(guó)救民的八路軍!
從此,李有源第一次用民歌唱出了歌頌共產(chǎn)黨、歌頌毛主席的歌子。
1942年冬大的一個(gè)早晨,夜幕向西漸漸地退去,一輪紅日從東方徐徐升起。在山溝里棲息了一夜的鳥(niǎo)兒,展開(kāi)歡快的翅膀,迎著朝陽(yáng),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飛翔……
一個(gè)身材魁偉的莊稼漢,頭上包著雪白的羊肚毛巾,嘴里哼著民歌調(diào),向蓖縣城的方向走去。這幾日,李有源一直在冥思苦想,他認(rèn)為自己編的幾首歌頌黨、歌頌毛主席的歌子,沒(méi)有更深刻地反映出自己和人民對(duì)黨和毛主席無(wú)比熱愛(ài)之情。因此,走在路上,他也一直在想著這個(gè)問(wèn)題,用什么來(lái)比喻毛主席的偉大呢?他走上一個(gè)山坡,忽然停住腳步,望著東方徐徐升起的太陽(yáng),興奮地自語(yǔ)道:“對(duì)!把毛主席比做太陽(yáng)是最好不過(guò)了……”黨和毛主席的英明偉大,正像這東方升起的太陽(yáng),紅光普照著大地,溫暖著每個(gè)勞動(dòng)人民的心房,引導(dǎo)人民永遠(yuǎn)向前進(jìn)!……想到這兒,他不由得笑起來(lái)。然后,甩開(kāi)大步,繼續(xù)向縣城方向走去。挑在他那厚實(shí)的肩膀上的兩個(gè)木桶,隨著那健壯的腳步、愉快的歌聲,前后飛舞起來(lái)……
陜北冬天的深夜,勞動(dòng)了一天的人們,已經(jīng)躺在熱呼呼的被窩里,進(jìn)入了甜蜜的夢(mèng)鄉(xiāng)。李有源并沒(méi)有睡,他正坐在炕桌前,借著明亮的油燈興奮地寫著。他用陜北著名的民歌“騎白馬”的優(yōu)美曲調(diào),完成了一首新歌《東方紅》:
東方紅,太陽(yáng)升。
中國(guó)出了個(gè)毛澤東;
他為人民謀幸福。
他是人民大救星。
《東方紅》這首不朽的傳世之作,從中國(guó)革命的搖籃──陜北傳出,便插上了翅膀,飛越黃河,跨過(guò)長(zhǎng)江,并漂洋過(guò)海,響遍了全世界。
精品視頻課程推薦
相關(guān)內(nèi)容
- 《木蘭詩(shī)篇》—歌劇的“中國(guó)式”勝利2014-9-24
- 羅西尼的歌劇處女作2014-9-24
- 《崔炳元音樂(lè)作品選》CD專輯品評(píng)2014-9-24
- 《乘夢(mèng)飛翔》賦予夢(mèng)想力量 2014-9-22
- 歌劇《居里夫人》:光與影 黑暗與閃光2014-9-5
- 普羅科菲耶夫的歌劇《戰(zhàn)爭(zhēng)與和平》2014-9-2
 名稱:中音在線
名稱:中音在線